我的姥姥于文连生于1924年2月4日,阴历是猪年的大年三十。我们常开玩笑说她是最小的猪,实事是她是家里的最长寿的人。
昨天下午妈妈来短信说:姥姥昨天去世了,我的泪水瞬间决堤。突然想起,前年秋天,在那个秋高气爽的国庆期间,在家里,我给她拍的最后一张照片的模样,那个收拾的干干净净的驼背的老太太走了,再也不会柔声细语跟我絮叨了。

(1990年秋,姥爷姥姥和我)
没有见过姥姥年轻时的照片,她也没留下青春年华时意气风发的模样给我们后人看。可能这也是敌后工作的需要,尽量避免留下痕迹。我印象中最早有她的照片,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拍的,那时候她六十多岁,姥爷还健在,我大概六七岁。照片中的姥姥个子高挑,坐的笔直,她把自己收拾得很利索,齐耳的短发别在耳后,眉宇间看得出她年轻时一定是个美女。
在上个世纪40年代那个战火纷飞的日子,瓜子脸、高鼻梁、双眼皮、大眼睛、身高一米七的漂亮的姥姥积极投身革命。在她十八岁的时候,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候,她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敌后做妇女工作。
姥姥从来没有跟我们小辈说过她年轻时候的事,所有关于她的事,有时候是从姥爷于富贵(一名同样在抗战最艰难时候入党、做敌后工作的老党员),或者后来是子女亲身经历拼凑起来的。用抛头颅、洒热血来形容他们那代人,我想绝不为过。作为经历过残酷战争洗礼的老党员,姥姥和姥爷口风特别严,从来不多说一句话,坚决保守党的秘密。所以关于他们年轻时候的事,对我们后辈而言所知极其有限。他们到底为革命做了哪些事,尽了哪些力,我们一无所知。他们也守口如瓶,你也别想从他们嘴里得到任何消息。那只言片语也是上世纪90年代后,在改革开放后的和平环境下有时通过语境透露的,这已经是格外开恩了。
通过姥姥的孩子们的亲身经历,我们知道,那时候,姥姥姥爷真的是为了党的事业,为了新中国的成立和建设默默奉献,从来不提任何个人要求,也没有一句抱怨。他们在任何的时候都相信党,相信组织,相信组织的安排。连姥姥的婚姻都是服从组织安排,为了革命工作而结合。
姥姥和姥爷都一米七多的个子,因很少顾及家庭和子女,所以,孩子们却都长得不高,而且身体不太好。1949年解放战争后期,因革命工作需要,姥爷准备随部队南下,接手被解放地方的后方工作,都做好了与姥姥分别和把孩子送人的安排,后来接到通知继续留下工作,这才留在地方。妈妈说,姥爷生前做过界石镇党委书记、人民银行主任,最后在县气象局退休。姥爷没在任何单位要过一套房子,姥爷的家一直在葛家镇池水头村的姥姥家。姥爷的家人都过世了,什么原因,没人知道,只知道姥爷的老家在其他村,哪个村,不知道。我想,像姥爷这样无家可归而又处处为家的共产党员一定有很多。

(1990年秋,姥爷姥姥与爸妈)
我小时候根本不知道姥姥姥爷很早就参加革命,一直以为姥姥姥爷就是普通农民。因为在我的印象中,姥姥姥爷跟所有朴实的村民一样都住在村里,姥姥姥爷的房子跟其他村民的房子连在一起,姥姥姥爷跟其他村民一样,自己种菜、挑水、掏粪、喂鸡、赶集……,我没看出来他跟其他村民有什么区别。如果说有不同,那就是:别的村民家都有地,而姥姥姥爷家没有地,我很奇怪姥姥姥爷为什么不种地,后来才知道原来姥姥姥爷很早就参加革命工作了。
即使后来姥姥九十岁了,上年纪后脑袋糊涂了,她不认识孩子们了,但是她依然挂念她的组织。我记得快九十岁的姥姥问我爸爸:她跟着孩子们住,她的组织关系还在村里吗?她叮嘱我爸去村里的时候一定要保存好她的党组织关系。这就是那代人的觉悟。革命的胜利、新中国的成立、国家的强大,我们现在的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也正是由那么多像姥姥姥爷这样舍小家、为大家的人不断努力无私奉献才取得的。
1997年夏天,姥爷离去的悲伤,让姥姥在姥爷坟前突发脑溢血昏厥,多亏抢救及时才没留下严重的后遗症。也是从那时候,姥姥开始在孩子们家轮流住,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她开始觉得孤独。离开了熟悉的环境,儿女们都上班,白天只有她一个人在家。
姥爷离世前,姥姥最喜欢串门、去河边洗衣服。姥姥串门有特点,喜欢在吃饭的时候进行。大家准备一起吃饭,最后发现她不在,姥爷轻描淡写来一句:肯定去串门了,不要管了,等我们吃完,你妈就回来了。姥爷离世后,在孩子们家,因为各种因素限制,也怕给孩子们添麻烦,她很少出门。在我家轮住的时候,当夏秋两季气候适宜的时候,妈妈怕她闷,每天会把她送到楼下让她跟老太太老头们一起作伴闲聊。大部分的时候,她只是坐在一旁一言不发,微笑地听别人说。
有一次,妈妈把她送下楼,一直不见她回来,后来妈妈出去找,发现她坐在石阶那,问她为什么不回家?她说我忘了家在哪了,只好坐在那等。可能就是从那起,姥姥的脑袋开始出现糊涂的症状,那时候她八十多了。
姥姥这辈子最发怵做饭,姥爷在的时候,在我印象中,姥姥家的食柜里永恒的有几坛糖醋蒜和芹菜花生米这样的咸菜,每次吃饭挖一碟出来。印象中的姥爷特别严肃,经常一言不发,吃着小咸菜,拿出一个小酒盅,自斟自饮。有时候爸爸带着新鲜的鱼和其他东西去看他们,吃完饭临走了,鱼还在水井旁放着没动,因为姥姥打怵做鱼。
记得我6岁时爸妈忙着工作,把我从城里送到乡下姥姥姥爷家读小学一年。那时候的我特别调皮,整个一个假小子,下河摸鱼,上山爬树,农田里乱蹦乱跳,带着外甥搞恶作剧,每天把自己弄得脏兮兮像个小花猫。经常到吃饭的时候,不见人,被姥姥四处找,最后捉住拎回家。现在回想起来,姥姥拎我回去,她训我的样子,觉得好温馨,那真是段快乐的时光。后来因为上学等各种原因,去姥姥那的时间少了很多很多,依稀记得大概每年暑假和过年能回去两次。但是,那段美好的时光已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那时候的姥姥虽然已经六十六七了,但在我能记事的印象中是她最年轻的时候,高高的个子,整个人收拾的很利索,齐耳的短发别在耳后。
姥姥这辈子,直到离世前眼不花,耳不背。姥爷离世后,由于跟孩子们住,她开始喜欢做针线活,到处收集我们的穿过带破洞的袜子补。我记得有一次,我的一只袜子破了个洞,她在洞那里攀线,绣出很漂亮的花。但是后来,随着她年龄的增大,最近两年她已经忘记她曾经会绣那么漂亮的花了。
在生命中最后的五年,姥姥变得越来越老顽童。经常会拿着她曾外孙的玩具在那玩,脑袋犯迷糊的时候,她大半夜拿着拨浪鼓波浪不停,弄得家人无法睡觉,姨们只能半夜爬起来没收她的玩具,顺便数落她几句,她会像个犯错的孩子一样默默不作声。
姥姥喜欢做针线活,后来脑袋越来越糊涂,总是忘记收针,她经常把针别在袖口,扎了二姨好几次。二姨一生气把针没收了。姥姥像个孩子似的委屈地哭了,一直到我家轮住的时候还闷闷不乐,妈妈看她一直不开心,问清楚事情原由后考虑到她的心情又允许她拿针。听到自己又可以拿针了,姥姥就像孩子得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东西开心了好多天。
白天洗好了水果,放在她面前,问她吃不吃,她总是说不要。等人一走开,她会悄悄一会吃一个或者一块,爸爸经常拿这个来逗她,她也会像个孩子般腼腆地咧嘴笑。
在生命的最后的两年,姥姥已经不认识自己的孩子们了。她会叫爸爸大兄弟,说妈妈是做饭的,喊姨是老太太。在她印象中,我永远是十七八岁在上学。我工作后,每逢过年,我会像我小时候,她给我压岁钱一样给她压岁钱,她会像孩子一样收到钱满足地咧着嘴笑,小心翼翼把钱放进干净的手绢里包起来,闲着的时候拿出来看看摸摸。结果,有一次我给她的压岁钱,她不小心玩丢了,她竟然着急上火起来,坐立不安,到处找。还好爸爸机智地找出一张毛爷爷放在书中夹着,安慰她把钱放在书里,是她忘记了,她才像个孩子似的安心了。
慢慢地,她越来越无法走路,起身的时候需要有人搀着。最近两年,她生活已经完全不能自理了,需要人照顾。半夜她睡不着,就不停呼喊,让妈妈和姨很辛苦。我最后一次看她是今年过年的时候,大年三十,我们给她买了生日蛋糕,给她带上皇冠。我发现她的饭量小了很多,瘦骨如柴,那么高的个子才八十几斤。我知道她是自然衰老。可是,现在她走了,我仍是忍不住大哭几场。想起我小时候她找我回家的场景,想起她以前趁我熟睡时,半夜老替我盖被子把我弄醒的场景,想起她上年纪后,我给她洗澡,督促她饭后吃药的场景……还是有很多不舍。
泪水中,我眼前浮现出我小时候她的样子,齐耳的秀发别在耳后,高高的个子,走得飞快。姥姥,这次您是去找组织了吧,在另一个世界,您跟姥爷团圆了,祝福您一路走好。(此文写于2015年5月6日,近期做过修改。谨以此文纪念我的姥姥和众多为新中国革命和建设默默奉献的先辈们。) 作者:山东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于玲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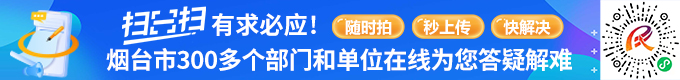



 2020年全国“放鱼日”同步增殖放流活动在烟
2020年全国“放鱼日”同步增殖放流活动在烟 山东滑雪高手汇聚“雪窝”烟台 赛场飞驰比
山东滑雪高手汇聚“雪窝”烟台 赛场飞驰比 2000余名民间艺人齐聚
2000余名民间艺人齐聚 以新姿态奔赴新征程
以新姿态奔赴新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