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的老屋悠悠在记忆深处,不时从梦境中走过,演绎了朦朦胧胧的少年故事,韵味悠长,让人深陷其中,不肯出来,犹如儿时贪恋冬天的热被窝……
老屋简约而清爽。四间青瓦房,三面碎石墙,数株梧桐树,构成了清清爽爽的农家院落。两只峨冠博带、气势不凡的芦花大公鸡,总是踱着四方步,优容地跟在四只母鸡后面,一副君临天下,舍我其谁的样子。猪圈里的两只猪崽,一只黑的,一只白的,慵懒地翻弄着食槽里的“残羹”,希望有能勾起它们食欲的美味。它们不时抬起头,从圈墙的缝隙中瞟一眼院子里自由着的鸡群,眼里流露出羡慕和不解,“同是家禽,差别咋就这么大呢?”老屋有些寥落,没有母亲忙碌的身影,也闻不到父亲轻轻吐出的、有些辣、又有点香的莫合烟的味道。双亲早已作古,他们为什么不肯与老屋一起走进我的梦乡呢?只是让这些旧物事在我的梦里隐约,平添了许多唏嘘和落寞。
记忆中的村落,总离不开那条悠远着伸向远方的古道。古道上斑驳着大车凌乱的印辙,这些印辙犹如年轮,在雨天里生长,在晴天里凝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记录着这个村落世世代代探索的步履。人们怀揣着梦想和希冀,沿着古道走向远方,去寻觅老屋所能赋予的斑斓。几度风雨,酸甜苦辣。有的被老屋所牵,沿着古道风尘仆仆归来,不论是衣锦还乡,还是行囊空空,无一例外都是乡情难抑,难免有“离乡愈近情愈切”的稚子之态;有的则在离开家园后,无奈把乡情交给了梦呓,魂牵梦绕时,一任泪水打湿了衾枕,老屋成了心中永远隐约着的感伤。
古道,固化在我的记忆里了,不知我的足迹是否还在古道的印记里!
儿时的记忆总在古道两边展开。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还不足以提供足够食物的年代,打猪草便是很多农家孩子放学后必须完成的作业。古道边水渠旁丰茂的水草,无疑是这些孩子趋之若鹜的所在。
渠水淙淙,滋润了渠边的花草,也疯长着河蚌的肥腴。
瘸腿六叔挽着裤腿,提着铁锹,一瘸一拐地沿着水渠寻觅。他六岁的外孙挎着小筐,在岸边随他蹒跚,一边走一边嘟囔,“老爷老爷,我饿,我要吃萝卜!”。瘸腿六叔看看渠边田里绿油油的萝卜,咽了咽唾沫,敷衍道“狗儿乖,咱不吃萝卜,回家老爷给你烀骚蛤(河蚌的一种,肉艮而腥)!”狗儿仿佛闻到了骚蛤的腥气,小小的眉头皱了皱,哭道“不吗!不吗!我饿,我要吃萝卜”。六叔看看面黄肌瘦,走路摇摇摆摆的外孙,又看看田里绿油油的萝卜,悄悄拭去眼角浑浊的泪水。他家成分高,本来就胆小怕事,怎敢打生产队里的主意。
看着这祖孙二人的窘况,心中隐隐作痛。向四周瞄了瞄,夕阳西下,牧牛倦归,我们的行踪在大自然的环抱里只是一声鸟鸣,只是渠中游鱼不经意地一跳,没人注意。我毅然跳过沟渠,毫不犹豫地拔了两个萝卜,仿佛听到了狗儿愉悦的笑声,喜滋滋地正要向草筐里放。一声断喝:“小兔崽子,好大的胆子”。抬头一看,妈呀!看山的麻六从田那边的桑地里窜出,像老鹰一样扑了过来。还没容我醒过神来,已被他结结实实拎着脖领提了起来,“熊玩意,熊心豹子胆,敢偷队里的萝卜!”,我一边挣扎着,一边大叫,“放开我、放开我,我不是给自己偷的!”。也许是念着乡情,也许是被我的话打动,他放开我,双目炯炯,“不是给自己偷的,难道是给我偷的?”。我嗫嚅着捻着衣角,指了指不远处的祖孙俩。看看狗儿细脖颈上硕大的脑袋,看山麻六轻轻叹了口气,默默地低下身子,将萝卜放进我的草筐,轻轻地说:“孩子,走吧!有善心,但要用好啊!”
……
不知是记忆成就了梦乡,还是梦乡延伸了记忆。悠悠的故乡总在不经意间进入我的梦乡。不知狗儿的梦里是否会有瘸腿的老爷、看山的麻六和那个曾给他偷过萝卜的少年?
(作者:林基强 书于2015年1月1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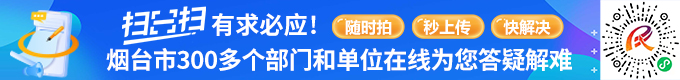



 2020年全国“放鱼日”同步增殖放流活动在烟
2020年全国“放鱼日”同步增殖放流活动在烟 山东滑雪高手汇聚“雪窝”烟台 赛场飞驰比
山东滑雪高手汇聚“雪窝”烟台 赛场飞驰比 2000余名民间艺人齐聚
2000余名民间艺人齐聚 以新姿态奔赴新征程
以新姿态奔赴新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