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一座城市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历史记忆。唐之记忆在西安,宋之记忆在开封,明清记忆在北京,百年中国的记忆在上海,改革开放的记忆在深圳……那么,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汉之记忆在哪里呢?我认为,必是长沙。风篷岭,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打开了这扇记忆之门。
或许,你没听说过风篷岭。然而就是这个小地方,在本世纪初却惊现出惊天秘密。以风蓬岭为首的谷山片区以及与之相连的戴公庙、咸嘉湖、天马山片区,共有汉长沙王及王后墓葬27座,其中谷山片区就有16座。在这片苍翠的青山下面,究竟是一片怎样恢宏的世界呢?神秘而又令人期待。
风蓬岭是个老地名,起于何时已无从考证;风蓬岭也是个小地方,一直以来,名不见经传,倒是风蓬岭隶属的谷山,却闻名遐迩。谷山与岳麓山比肩,自晋唐以来,就是佛教名山,山中产一青石,可制砚,曰谷山砚。据清乾隆《长沙府志》记载:“谷山,县西七十里。山有灵谷,下有龙潭,祷雨辄应。有石色淡青,纹如乱丝,叩之无声,为砚发,亦有光。”谷山砚备受宋代书法家米芾推崇,米芾《砚史》记载:“潭州谷山砚,淡青、纹如乱丝、扣无声、得墨快、发墨有光。” 风蓬岭地处谷山北向风口,素来风多,故名风蓬岭。南方冬季,喜吹西北风,夏季,喜吹东南风。冬天,当凛冽的寒风欲进入谷山腹地时,风蓬岭是迎风的第一站,任北风呼啸,风蓬岭如鼓起的风蓬,迎风屹立,经此遮挡,风势渐弱,风速渐减,至谷山深处,已全无寒意;夏天,东南风从山谷穿过,至风蓬岭时,它又如张开的风蓬,作最后的挽留,山风顿成回旋之势,谷山又多留住了一股最后的清凉。得此天然优势,谷山也素有洞天福地、世外桃源之美誉。两千多年来,风蓬岭就这样默默地守护着,不卑不亢、无声无息,谁也不知道它的高贵,谁也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知道它叫风蓬岭的,也就是邻近的数十户居民。
我第一次听说风蓬岭,是在2005年。当时,一房地产公司在风篷岭一带开发房地产,发现一汉代古墓,经考古专家勘测,属汉代长沙王室墓葬。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呀!站在风蓬岭上,一眼望去,均是连绵的小山包,据考古人员介绍,居然全是历代汉长沙王和王妃墓葬。两千年来,守护谷山这一洞天福地的竟是汉长沙王和王妃。人们不禁惊诧!
风蓬岭的重大发现,震惊了考古界。1972—1974年发现的马王堆汉墓曾被评为“世界十大古墓稀世珍宝”,入选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马王堆汉墓共三座,仅是汉代某长沙王丞相轪侯利苍及其妻子、儿子的墓葬。而以风蓬岭为首的片区,竟是汉长沙王国的君主和王妃。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均属罕见。但遗憾的是,风蓬岭的重大发现,也惊动了盗墓贼。2008年,长沙古玩市场出现了长沙王印的传说,一起“鬼吹灯”的故事也在土夫子(盗墓贼别称)中疯传。这些现象,引起了文物部门警觉,经走访发现,风篷岭二号长沙王墓已经被盗,市场上传言的汉代金印很可能就是从此墓中盗走。后来,虽经公安全力侦破,“鬼吹灯”案告破,长沙王印等国宝级文物得以追回,但古墓却受到极大的破坏,留下的遗憾永远无法弥补。
2013年,汉长沙国王陵遗址被列为国家第七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后,又被列入代表中华文明的150处大遗址名录。再后来,市政府准备修建汉长沙国考古遗址公园,规划了2.12平方公里。今年3月,长沙市委对加快汉王陵保护建设又提出了新的要求。暮春时节,我听说遗址公园一二期已基本建成,特约前往,想再次感受长沙城的汉韵,汉韵中的长沙。

汽车过湘江,从三叉矶大桥下,向北,驶入银杉路。左边郁郁葱葱,浓荫遍地,影影绰绰的山包就像一个个睡意未消的湘女,披着暮春时节雨雾之后的蝉翼薄纱,脉脉含情,凝眸不语。都说湘女多情,雨雾中的小山包同样令人遐想。由于数年前来过,感觉每个山包都像风蓬岭,数次左拐进入上山小路,数次登上形状差不多的山包,数次问道于当地居民,都说,这里就是汉王陵。但从山中散落的民居即知,这里虽是汉王陵辖区,但绝非已建好的遗址公园。如此反复,终于看到了遗址公园大门,公园负责人马主任早在大门口等候。马主任中等身材,微胖,之前我们有过交往,也知他是一个有情怀的文物守护专家,一直潜心于汉长沙国研究。说起汉长沙国,他便激情满怀,滔滔不绝,旁人根本插不上话,眉宇一舒一颦,一张一蹙,蕴藏着丰富的感情。公园大门朴素,仅右侧立一高数丈、灰色、内空的立柱,立柱上有类似屋面的顶,柱中嵌一黑色条状、看似木质的通栏材质,上书几个大字,“汉长沙国考古遗址公园”。早期汉隶、古朴典雅、几分简帛韵味,与环境相得益彰。建筑简洁明快,可能是从汉代一种典型建筑“阙”中抽象提炼而来,以细高的体态冲破以水平铺陈为主的建筑平衡,产生蓬勃向上的动感和激情。我没问马主任这建筑的设计理念,既然心中已有认同,又何必去求证呢?从心而览,感无不通。
进入大门,数十步开外,便是王陵缓落的坡角。建设者别具匠心,削坡砌墙成壁,壁上青铜浮雕,浮雕后是密植的树木,树和浮雕恰似入门照壁,有效遮挡了参观者的视线,否则,入门即是王陵,既显突兀,又没有中国园林曲径通幽之趣。马主任领我们走近浮雕,浮雕由三个故事组成,分别是“吴芮受封”“刘发筑台”“降国为侯”。三个故事,讲述着汉长沙国由立到废二百二十年的历史。
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建立汉朝,改秦郡县制为郡县与封国并行的“郡国制”。嘉奖吴芮,立以为王。据《汉书·异姓诸侯王年表》记载:“九月,初置长沙国,……十月,芮徙长沙。”纵观汉初所立诸侯国,实则为巩固汉初之统治。《史纪·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云,“何者?天下初定,同姓骨肉少,故广强庶孽,以镇抚四海,用承卫天子也。”长沙国的建立,一个重要原因是防御南越。《史记·南越列传》记,“秦已破灭,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高帝已定天下,为中国劳苦,故释佗弗诛。”佗即南越王赵佗。汉在南越北侧设立长沙国、淮南国,既可作进攻之基地,又可作退守之缓冲,实为防南越之屏障。如果说,吴芮封王,立长沙国,既因吴芮功劳甚巨,又为抵防南越,是汉初立国之要,那么后来,刘邦平定韩信、彭越、黥布等异姓诸王,刑白马盟誓,“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而独留长沙王,何也?确也值得深思。

据《汉书》记载,“初,文王芮,高祖贤之,制诏御史:‘长沙王忠,其定著令’。至孝惠、高后时,封芮庶子二人为列侯,传国数世绝。”另载,“欲诸王之皆忠附,则莫若令如长沙王。”可见,长沙王忠,是上下认同、自始至终的,不仅高祖如此说,惠帝、吕后也都认可。长沙,自古就是爱国忠君之地。早在吴芮之前七十多年,屈原就行吟于湘水、沅水间,留下了《离骚》《九歌》《渔父》等不朽诗篇。公元前278年,秦攻破楚都郢,屈原作《怀沙》,投汨罗江而死,史称“屈长沙”。屈原忧国忧民、忠君报国之心可昭日月。吴芮之忠,是否受屈原影响不可得知,但吴芮因忠而得善果却是不争事实。而彭越、英布、臧荼等徼一时之权变,以诈力谋取成功,咸以裂土,南面称孤,终遭灭亡。也有人认为,是吴芮甘于平庸,终免于祸。我不知作此评价者对平庸作何解释?如果说甘于平庸,是种胸襟品德,是份智慧福祉,那么吴芮确实甘于平庸;如果把甘于平庸理解为平庸之辈,则实不相符。
吴芮生于公元前241年,正处于秦兼并六国、战事频发、社会动荡、灾难频仍的战国末期。秦统一后,尚未安定又迅转急下、变本加厉、严刑峻法、繁徭重役,致使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盗贼兴起、烧杀抢掠。吴芮为保卫家乡免遭涂炭,乡亲免受伤害,组织家丁亲兵抗击流寇。年仅十八岁就招募兵马一万多人。吴芮藏兵于民,闲时为民,战时为兵,兴农兴商,自给自足,军纪严明,很受百姓拥戴。他大胆革除弊政,轻徭薄赋,减轻百姓负担;带领百姓兴修水利,制定一系列鼓励农耕的措施,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民众赠号“番君”。公元前209 年7月,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起义。8月,吴芮第一个起兵响应,出兵横扫赣、湘、桂一带,威镇江南。公元前204年,吴芮取长沙后,在湘水之滨,修筑长沙古城。当时,北方兵荒马乱,长沙平静祥和,大量商家南下长沙,长沙赢得空前繁荣。如此文治武功,岂是“平庸”之辈所为。然功成之后,吴芮处事低调,精减军队,把大部分领地让给刘邦子女,安排第五子吴元带部分家眷回浮梁瑶里生活,以忠诚宽厚之心换得家族之平安、辖区百姓之福祉。这种胸襟和智慧,又岂是“平庸”二字所能概括呢?
吴芮之举,后人赞誉甚多,以宋为盛。宋人华镇,路经鄱阳,缅怀吴芮,“秦吏方摇毒,君王独得名。国虽为地小,忠亦自天成。秘殿似容悴,立堂草木荣。兴亡何足道,青竹有嘉声。”南宋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夏,岳飞奉诏去杭州临安,从九江过鄱阳,特地到番君庙凭吊吴芮,岳飞感慨题联:“机关不露云垂地,心境无暇月在天。”岳飞以“精忠报国”感召后人,对吴芮之忠也甚为赞誉。

吴氏长沙王,传五代五王,至文帝后元七年,即公元前157年,长沙王吴著无后,国除。景帝前元元年,即公元前156年,“复置长沙国”,次年,封庶子刘发为长沙王。刘氏长沙王传八代九王,于公元9年,王莽篡汉后废除。东汉光武帝时,又复封刘舜之子刘兴为长沙王,从公元26年至37年,在位十二年,后降为临湘侯。
刘氏长沙王,最有故事者,当属定王刘发,以孝闻名。相传,刘发是因一场美丽的误会而降临皇宫。刘发生母唐姬,是汉景帝嫔妃程姬的侍者,某夜,景帝召见程姬,程姬因身体不适,叫侍女唐姬顶替,景帝酒醉不知,后生刘发。 刘发聪明睿智,封长沙王时,仅辖长沙一郡,只吴氏长沙王五分之一。据《太平御览》记载,“景帝后二年,诸王来朝,有诏更前称寿歌舞。定王但张袖小举手。左右笑其拙,上怪问之,对曰:‘臣国小地狭,不足回旋。’帝以武陵、零陵、桂阳属焉。”自此,长沙国辖今湖南全境。
刘发任长沙王27年,至仁至孝。仁者,执政以仁,经济发展,百姓安居乐业,曾八次觐见天子述职,均获赞誉。特别是对安抚属国南越,稳定西南功勋卓著,故谥号为“定”,史称定王。孝者,刘发至长后,日夜思念远在长安的两个母亲—程姬和唐姬。汉时,洞庭湖区水稻已负盛名,每当新谷收割时,刘发定要运米远赴长安,请母亲品尝新鲜大米,再嘱使者运长安故土返回,于长沙城东高处夯土筑台。年复一年,故土筑成一座高台。多少回夕阳西下,刘发登台北望,遥寄思母之情。定王筑台望母,心存孝心,所以,“定王台”也被人们称为“望母台”。
后来台废址存,名称延续至今,供后人凭吊传颂。北宋朱熹曾作《定王台》诗,“寂寞番君后,光华帝子来。千年馀故国,万事祗空台。日月东西见,湖山表里开。从知爽鸠乐,莫作雍门哀。”清光绪元年,湖南粮道夏献云重修定王台,重修碑记中写道,“湖湘人尚气节,风俗敦厚。虽乡愚僻壤,谈某也忠,某也孝,辄勃然色动。盖其崇根本,渐摹成化久矣。而其千古不磨者,忠莫著于贾太傅,孝莫著于长沙定王,一宅一台,岿然独存。”夏公此番评论,当是最好的总结。
浮雕前,我沉思良久,长沙国的历史在眼前演绎,我好像听到了芮王时金戈铁马的撞击嘶鸣,也好像置身于血色残阳中,登台望母,“西望长安不见家”的空旷悲悯。是呀!历史长河,浩浩汤汤,岁月洗涤了多少尘埃,浪花淘尽多少英雄。一切众生都在现实而又虚渺的时空中淡去。或如流星般划过,璀璨一瞬;或如落叶般飘零,无息无声。时空依旧,逝者如斯。然而,就在这种循环往复之中,历史的积淀竟有如此的韧劲和力量,数千年来生生不息。这中间,有多少触动心灵的因缘,多少看似无痕的因果,无从考究,也不得而知。然唯忠唯孝,自有生命以来,其聚合的力量,跨越时空的张力,历经沧桑的韧性,总会在某一个时刻,在人心中荡起涟漪、激溅浪花、点亮心灯。

从浮雕墙左拐,便是一条迂回曲折、拾阶而上的长廓。长廓两边,皆为长沙国时,各级地方官吏之印拓,或用朱砂印文,刻于两侧青铜墙壁;或选一丁字湾麻石,拓印留痕,立于扶栏宽阔之处。印皆阴刻、平整端庄、规整宽博、浑朴自然,一看就是汉印风格。其中也有风格迥异之印,如“武冈长印”,似手写简帛,生动自然,如鹤立鸡群,也别有风趣。马主任见我在“武冈长印”前停留,遂介绍到,汉时,郡下设县,大县称“令”,小县称“长”。武冈为西汉文景期间所置,隶属长沙郡,小县,万人以下,故称“长”。至于此印为何不同于其他官印平正规整,马主任也说不出缘由,可能也是汉文化之多元、大汉气象之包容吧!
“武冈长印”之后,连着三个印,“临湘丞印”“临湘尉印”“临湘令印”。临湘系长沙国都城,古称“临湘故城”,是吴芮封长沙王时,在战国长沙古城基础上修缮而成。临湘令,掌治临湘县,管辖地应是围绕临湘故城的广大区域,其位置极为重要。县丞和县尉,一文一武,协助县令工作。由此推断,汉初时,官僚机构尚简,尊崇黄老,无为而治,民顺国宁。
在众多印中,还有两印置于廓首,即为廓道入口,一为“兴里乡印”,一为“都乡啬夫”。秦汉时,郡、县、乡是国家的基本行政机构,乡下设里,里为居民自治组织,不属政府机构,就如同现在的市、县、乡,乡下设村,村亦为村民自治机构。乡,上承县,下治里,行政长官曰啬夫,相当于现在的乡长。我不得不佩服这个官名取得好。“啬夫”在《说文解字》中有四种意思,一曰农夫,二曰从事一般劳役者,三曰农神,四曰俭省节用之人。作为直接管理农户的政府官员,不就是这四项职责吗?既是农业的管理者—农神,又是劳动者,且是个懂农业的劳动者—农夫,还是带头勤俭节约之人。
里如同现在的自然村落,集聚成里,一般管辖十余户至百户不等。里的负责人为里正,由居民推选德高望重之人担任,如同现在选村主任,不属政府官员。里以下,还有十长、五长,分别管理十户、五户人家。里的管理很规范,一点也不亚于现在的物业小区管理。每个里都有一个出入的总门,白天开,夜晚闭,管门者称里监门,形象直白,一听就明白是干什么的。里监门一般由里中困难居民担任,工资由大家分担共兑。可见,帮扶弱者、协同自治一直是中国人的传统管理模式,不论是沿袭数千年的家族宗祠管理,还是村规民约自治,庞大的社会历来就不乏管理者。或许,越是基层的,越是科学的;越是大众的,越是管用的。
马主任一步一台阶,边介绍边指引。我边看边听边聊,聊多了也就发现了一些规律。基层组织的印安放在起步台阶,台阶越高,印所代表的官职就越大,台阶尽头,及顶之处,想必就是“长沙王印”了。难怪入口处两边第一印分别为“兴里乡印”“都乡啬夫”。我笑问马主任,这条台阶汉印步道,是不是寓意登临者步步高升呀!马主任正在兴头,欲深入解读,我笑而打断了他的话。我说,其实倒过来也未尝不可,大人物不必都高高在上,把群众举过头顶的人,才真有一双巨人的肩膀。

沿汉印步道及顶,俯瞰谷山深处,一座座小山包相对独立,却连绵成势。蝉翼般的雨雾开始褪去,山显得更加青翠。太阳从云缝中洒落,点点滴滴播撒在山头,光影在青翠中跳跃,一闪一闪,像是挑逗,有几分俏皮,又像是害羞,反复躲藏遮掩。我喜欢这灵动中的青翠,它于宁静处蕴藏生机,就像熟睡中的婴儿,虽然安静,却生机勃勃。马主任指点着远处的山包,不无自豪地介绍,每一个山包都是一处王陵,每一个山包都是一座宝藏,山包下面是一个怎样恢宏精彩的世界,至今都无法想象。即使展开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可能都无法企及之毫厘。马王堆汉墓呈现的奇迹,已经让人始料不及了,而这片群山,是马王堆汉墓的历代主子。马主任的介绍让我激动不已,透过青翠的群山,我好像看到了群山深处精彩纷呈的世界。
汉初六七十年间,统治者推行黄老之术、无为而治、与民生息,经济社会得到空前发展。特别是文帝景帝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出现了第一个盛世,史称“文景之治”。据《史记·平淮书》记载,文景时,“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这是一幅多么富足的画面呀!无论城市和乡村,钱满库、粮满仓,物质如此丰盈,人民自然幸福美满。
马王堆汉墓曾出土了一百个竹笥,其中七十八个装有各种粮食种子,稻、麦、黍、粟、大豆、赤豆、麻子等,无所不有。可见,当时各种作物的种植已遍布乡野。随葬的水果、药材种类之多,也令人惊叹。随葬的肉食品都经过精心烹调,烹饪技术精湛,调料繁多、工序复杂。如此丰富的食物出土,足见汉初长沙农村的兴盛发展。
马王堆汉墓中,让人惊艳的还有绚丽多彩的丝织品。其数量之多、品种之全、花样之新、保存之好,在考古史上均属罕见。不同工艺搭配不同颜色,现已发现的颜色就有三十六种之多。如此排列组合,我无法想象那个五彩缤纷的丝绸世界究竟有多么绚美,其精细化程度,又岂是“工匠精神”四字可以概括之。尤为令人惊叹的是,马王堆一号墓中出土了三件襌衣,两件素纱,一件白绢。其中一件素纱襌衣身长160厘米,通袖长195厘米,而重量仅仅48克,不到一两,如果除去袖口和领口较重的边缘,重量只有25克左右,折叠后可以放入火柴盒中。真是轻若烟雾、薄如蝉翼呀!湖南省博物馆曾委托某研究所做过有趣的尝试,复制素纱襌衣。研究所用现代人眼光、高科技手段复古汉代工艺,复制出来的第一件素纱禪衣重量超过80克。之后,专家们从养蚕开始,高精度控制每一个细节,呕心沥血13年,终于织成了一件49.5克的仿真素纱禪衣。
当思绪从遥远的汉代回归,再次放眼于眼前这片青翠山峦时,阳光显得更加灿烂。我曾有幸在省博物馆目睹了素纱襌衣的风姿,此刻,我好像看到了一群轻曼的舞者,身着素纱禪衣,在群山间曼舞。如雾、如烟、似有还无的襌衣,在曼妙的舞姿中尽显空灵。我想,如果敦煌的飞天也能着此禪衣,那会是一个怎样更加玄妙的世界呢?

群山深处的传奇,令人遐想;蓦然回首步道反侧,一座巨大的王陵突然跃入眼帘,竟也令人猝不及防。感觉就是远处的某座山包,突然来个乾坤大挪移,拦住你的去路,横亘于眼前。我惊诧于这由远及近的视觉冲击,仔细打量突显于眼前的王陵。王陵是一座完整的小山,小山修复成方锥台状,山上覆盖着一层郁郁葱葱的小草,显得生机勃勃。步道在半山腰绕山一周,再缓缓而下,与陵下道路相接,直通遗址公园深处。我问马主任,这就是风蓬岭王陵吗?马主任说,这不是风蓬岭,这叫桃花岭,风蓬岭与桃花岭并肩,风蓬岭居北,桃花岭居南,手牵手面向湘江。过去,从湘江登岸西眺,一眼就能看到二岭,一曰桃花岭,至阴至柔,娇艳妩媚,一曰风蓬岭,至阳至刚,粗犷豪迈。二岭如同兄妹,又似夫妻,携手并肩,朝迎湘江红日,暮看月映江心,一诺竟是两千年。遗憾的是,早些年,风蓬岭因开发而毁。
马主任不再言语,大家都保持着沉默,只有随行的几双高跟鞋,发出有节奏的咔嗒声,不知道是在敲叩着地宫大门,还是在向两千多年前的时空发送电报密码?突然面对两千年前的遗址,我顿感时空被压缩成了一个饼,我们与两千年前的距离难道就仅此一层薄薄的土吗?人生百年,在历史长河中何其短暂,比较起来也就是一个闪电那么长的瞬间,但历史就是由这样一个一个的瞬间接续传承而成,我无法判断人的一生是伟大还是渺小。从瞬间而言,肯定是渺小的,但某些瞬间却像闪电一样照亮长空,像炸雷一样响彻云霄,虽然短暂,但绝不渺小。王陵深处,或许就是生命伟大的见证,也是汉韵长沙最铿锵的证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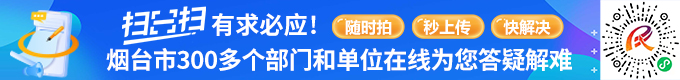

 2020年全国“放鱼日”同步增殖放流活动在烟
2020年全国“放鱼日”同步增殖放流活动在烟 山东滑雪高手汇聚“雪窝”烟台 赛场飞驰比
山东滑雪高手汇聚“雪窝”烟台 赛场飞驰比 2000余名民间艺人齐聚
2000余名民间艺人齐聚 以新姿态奔赴新征程
以新姿态奔赴新征程
